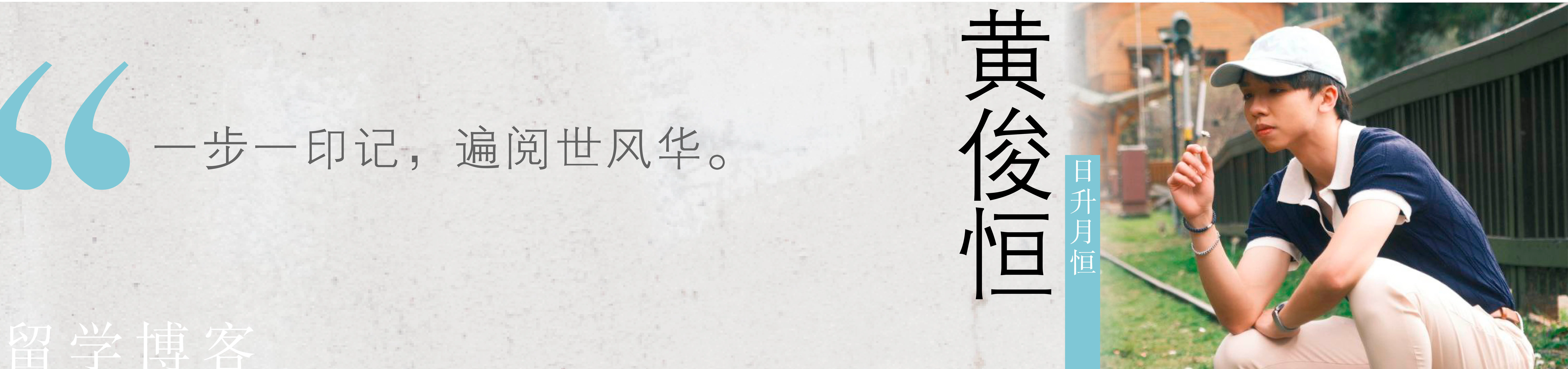不久前,我和几位在北大认识、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,聊起在中国的社交圈与交友心得,才发现大家的经历大同小异,遇到的问题却又各不相同。在前往北京之前,我对未来的社交圈的想象,大概就是大学里的朋友大多数会是新加坡同学,真正融入本地学生的核心圈子会很困难。
其实这并不是我刻意给自己设限,而是种种因素叠加,让我在社交上心里多了几分顾虑。刚升上大学的本地同学,大多刚从高压的高考和紧张的学业环境中走出来,这和新加坡的校园氛围非常不一样,也是留学生比较难走进本地学生的圈子的主要原因。
当兵两年后再回到校园,我更是对校园里的社交显得无所适从。再加上留学生宿舍本就与本地学生分开,使我一度认为没有踏出社交舒适圈的必要。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同班同学就曾和我说,开学前不少学长学姐都提醒她:“留学生很难和大陆学生交朋友。”
她承认和大陆学生确实存在隔阂,不仅有文化上的差异,也常常缺少共同话题。但她也意识到,刚进大学时大家其实都彼此陌生,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。如果总是被动等待别人来找自己,恐怕很难真正建立联系,因此主动一点格外重要。
细想来,我在校园里结识朋友的途径大致有三种,而不同的环境往往也塑造了不同的相处模式与友情性质。首先,初到北京时最先接触到的,自然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。
这种友谊建立在“同为异乡人”的基础上,大家都背井离乡,在陌生的环境里彼此依靠, 在一起时还能听到熟悉的“乡音”。我们的生长环境相同,因此很多“不习惯”甚至“看不惯”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。这样的友谊往往超越了学业,更贴近生活。尤其在生病或受伤时,他们往往是我第一个会想到去求助的人。

第二个途径是通过一起上课认识的同学,而这类朋友又可以分为两种。第一种是同院系的同学,主修课程大多重叠;第二种则是选修课上结识的外院系同学,通常因为小组作业或互相分享课堂笔记而认识。
坦白说,我通过这个途径结识的朋友并不算多。同院系的同学虽然见面的机会最多,但难免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。尽管留学生没有保研或入党入团的压力,但在考试优秀率、有限的实习机会等方面,仍然需要和本地学生比较。
至于外院系的同学,除了那一门共同上的课,平时几乎没有交集。等课程结束后,再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,因此交流往往带有很强的现实需要,更多是围绕完成作业,或一起复习等共同利益展开。
不过,现实需要的合作与真心的友谊并非完全对立。就拿我同院系的朋友来说,最初确实是因为一起上课、做小组作业而熟悉彼此,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渐培养了默契和信任。但随着交流的深入,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学业之外的共同话题,于是这份关系便自然地延展到课室之 外。

第三种途径则是通过社团或各类校园活动结识的朋友。这类友情往往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与追求之上,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功利目的或竞争关系。这样的相处更加轻松自在,没有太多负担,也让我更能放下戒备,做最真实的自己。
中国学生普遍更“卷”,在交友上也更偏向内向。这两者之间或许相关,甚至可能有因果关系。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,交友的契机可能不是纯粹的缘故,但真正能让一段关系长久维系下去的,却一定是最纯粹的心意。
不确定是因为留学的缘故,还是随着年龄增长心智更趋成熟,我渐渐发现自己和许多同龄人都对所谓的“无效社交”颇为抗拒。这并不是功利心作祟,也不意味着每一次交流都必须带来具体的成果,而是更在意相处能否真正触及内心。
如今的大学生承受的压力已够多,有来自同侪之间的比较与竞争,也有来自自我期待的不断加码,这些往往会带来焦虑和内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“有效社交”的意义就在于,在有限的精力里,把时间和心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关系。维系一段友谊,并不是靠共处时长来衡量,而在于相处的过程中,是否能够进行真诚而有价值的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