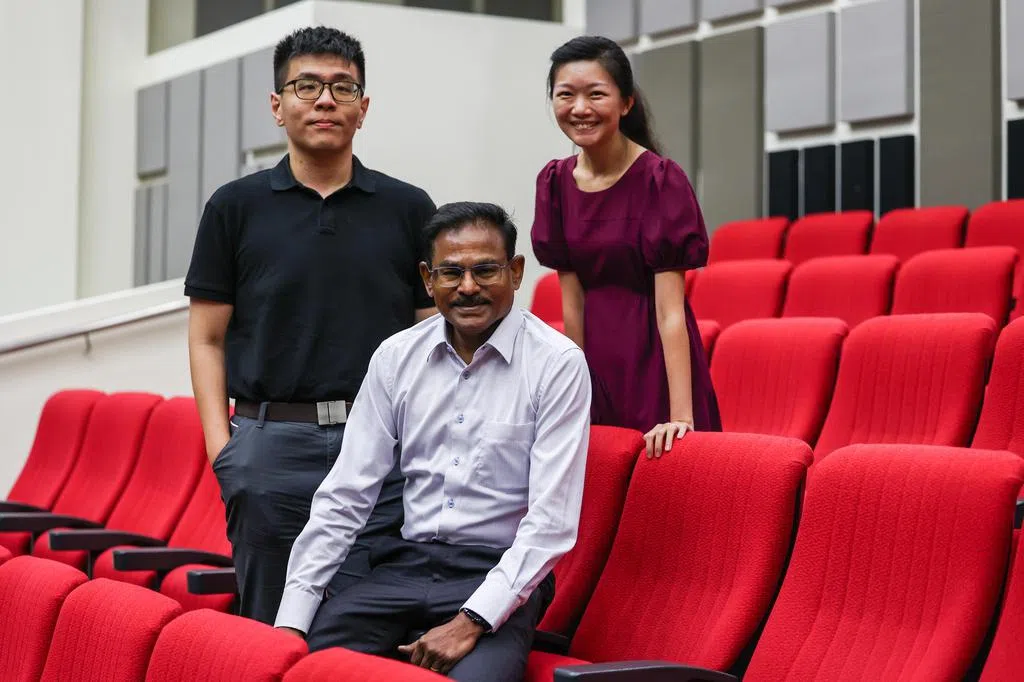教育改革须拿捏时机,教育部长陈振声以分流制度和双语政策为例,讲述决策者当年落实这两项政策时,如何因时制宜,分别采取一急一缓的不同策略,按社会转变步伐,调整执行的速度。
陈振声星期二(2月11日)在一场教育讲座发表演说,回顾新加坡自二战后以及独立以来60年的教育体制发展历程。他说,决策者在落实教改的过程中,须懂得判断时机。
“时机是最关键的。我们须具备敏锐的直觉,知道何时须坚定信念,引领大家前行;什么时候又应该运用智慧,根据社会转变的步伐,调整执行政策的速度。”
以分流制度来说,陈振声指出,在1979年时,社会虽未广泛接受这个政策,时任副总理吴庆瑞以及其他建国元勋仍决定推行。
“不推行这项政策,在政治上远远更有利。但这也意味着,我们会面对高辍学率和识字率低的问题。最终,这对教育体制或整个国家来说,都是不利的。因此,我们做出权衡,以短期的损失,换取长期的利益。”
他指出,分流制度根据学术和语言能力,将学生编入不同源流,让学生按各自学习进度和强项,接受教育和栽培,几年后极富成效,辍学率大为降低,学术成绩也明显改善。
然而,随之而来的学业竞争、对分数过度重视,以及学生无形中遭标签化等现象,多年来让分流制度备受批评。2024年,本地中学全面实施科目编班,取代分流制。
陈振声说,待时机成熟,也就是学校具备能力和资源的时候,教育部让学生过渡到科目编班计划,以缓解标签化现象,回应学生的不同志向和期许。
另一方面,即便我国对教育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,双语政策始终是教育制度的基石。陈振声说,政府当年推行这项语言政策时,选择渐进而非速成的方式。
“我们并没有立即关闭母语学校,而是等待条件成熟。我们是在启动双语教学近20年后,才将英语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用语。”

我国早期的学校分为英校、华校、马来学校和淡米尔学校。1959年,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时,半数学生就读母语学校,他们相对较少有机会锻炼英语读写能力。此外,各语言源流学校有各自的课程和考试要求。
随着英语能力在就业市场占优势,以及为了避免语言断层线加剧,自治邦政府在1960年推行双语政策,规定小学生必修英文,中学则在1966年实施。
陈振声说,当时不能仓促执行在学校推行规范化的语言政策,须等待合适的时机,以及经济环境和家长的选择发生转变。
“思维的转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。逐渐的,家长认识到,能用英语沟通的学生,就业前景更好,也就相应地为孩子报读英校。到了1984年,非英语源流课程招收同届不到1%的小一生。政府那时才开始将学校教学用语规范为英语,并在1987年完成这项工作。”
但他指出,人们的思维和社会文化也须改变。如果人们不拓宽对成功的定义,无论教育部如何推行教改,都无法减少学生的压力,也无法让学生的多元才艺受到肯定。
须营造开放持续及具有温情唯才是用制度
陈振声强调,我国须营造开放、持续以及具有温情的唯才是用制度,让人们根据各自强项发挥潜力。他提醒,政策也须不断更新,维护社会流动性和凝聚力。此外,他也呼吁教育界维持团结。
他说,我国独立60年来克服重重挑战,本地教育体制下来的任务,除了协助每个学生发挥潜力,也要激励他们不畏挑战、勇敢前行,为新加坡做贡献。
这场题为“从基础发展至前沿——我们的教育之路”的讲座由教育部、国立教育学院,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联办。约500人出席讲座,包括教育部和政策研究所代表、国立教育学院教职员和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应届毕业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