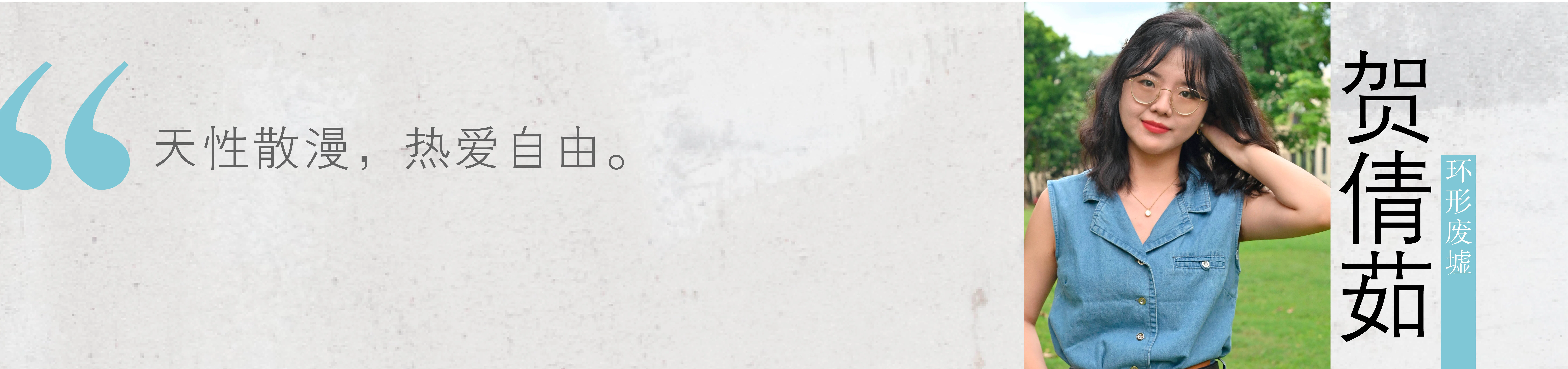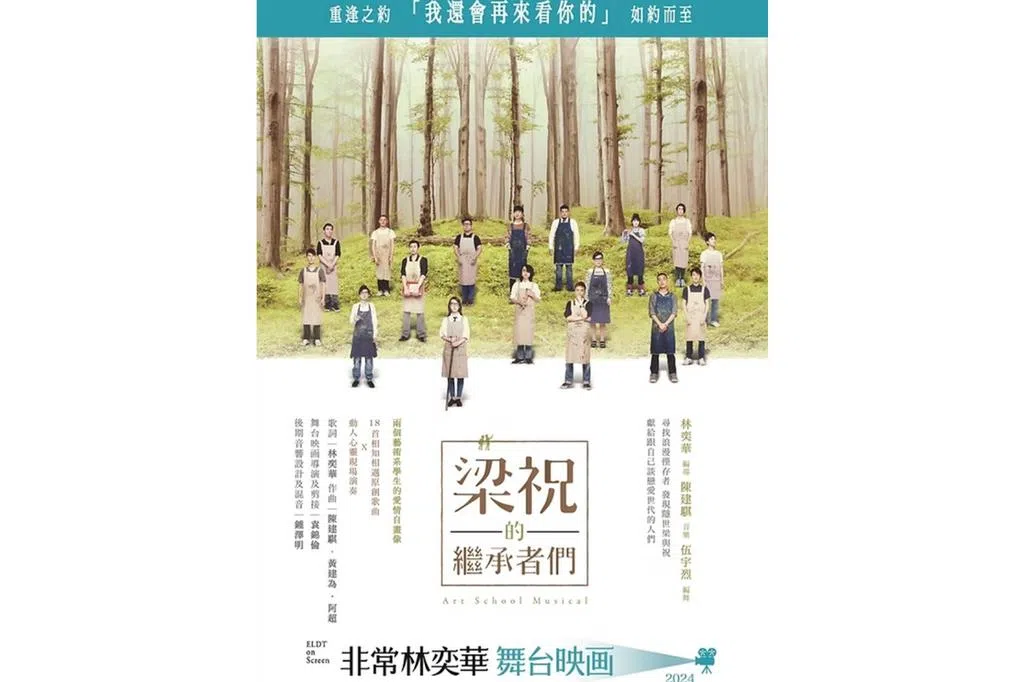朋友们都知道,我近两年的生活重心完全在博士研究的课题上,我的研究对象是新加坡华文长篇小说。我并不想在博士论文中做片面或二手的判断,因此,我对自己提出要求,要读完从1936年到2015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所有华文长篇。
这是一个繁冗的过程。我不知是研究对象的缘故,还是成为博士的必经之路。总之,年轻人还是不要轻易产生做文学史的野心。没有任何筛选,想要一猛子扎进原生文学的海里,很容易陷在岸边冗长的滩涂里,偶尔被粗糙的礁石绊住脚;往前走会被浅海的群鱼困住,在浑浊的水里,听它们讲毫无叙事技巧的八卦;玳瑁龟或儒艮实属罕见。我有时候宁愿站在岸上,听AI老师讲八百遍美人鱼和王子的幻想故事。
直到1987年。
我是完全按照书籍出版的时间顺序在阅读新华长篇,直到读到英培安于1987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,我才像真正游到了文学的海。斑斓的珊瑚和生动的游鱼,透明泛蓝的海水里还有一缕来自北方凌冽的风。
其他的作者在小说里写南洋地,铜臭天。写幼稚的头脑里,塞满了魔鬼般的金钱。写我要读书,我要文凭,我要上大学,我要找个好工作。
英培安:“诗人是不需要文凭的。”
这部小说的男女主分别叫涓生和子君。
子君讽刺涓生:吊起来都滴不出半滴墨水。
涓生反驳:难道非要满嘴都是米歇尔·福柯、李维·斯特劳斯或马尔库塞才算有墨水吗?这些结构主义除了让一些好卖弄的人用来装饰他的空洞的谈话外,我看不出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用处。
子君回击:马尔库塞和结构主义拉不上关系,正如你和墨水一样。
在英培安对文学典故的借用和引用中,在男女主角机敏的交锋中,旁人一眼便能看出,这是英培安写给文学青年的情书。
或许,你不喜欢近乎掉书袋的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》。但你看,他细致的遣词,写“我”和闹钟是“一对孤独的怪物,互相倾诉自己的寂寞。”他精确地比喻“他们看不到别人的烦闷在生长,如同看不到草的生长一样。”他幽微地观察到在食阁卖彩票的中年妇人,“她的笑脸像个面具,已永远贴死在她的脸上,即使她如何痛苦也扯不下来了。”他小说里的女性角色,可以跳出故事结构来质问:“我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,让作者,尤其是男性作者书写我呢?”放在女性主义批判盛行的今天,他也是位性别意识先锋的男作者。且他清醒又坦诚地认识到:“你并不比其他读者更了解你笔下的人物,就像你不比别人更了解你的儿女一样。”
我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,才抵达樟宜机场,来新加坡求学,于2022年正式开始研究新加坡文学。可英培安先生在2021年初就去世了。
他的作品在新加坡这个岛上好得太难得了,好到,当我终于读到他的小说时,竟生出一种与英培安擦肩而过的惆怅。
但是还好,我们还有文学。